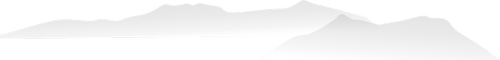
五十多年前,我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。我那时是二十岁上下。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,在清华大学兼课,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吧。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,实际上就是美学,这是一门选修课。我选了这一门课,认真地听了一年。当时我就感觉到,这一门课非同凡响,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,比那些英、美、法、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。
——季羡林
季羡林先生所说的“孟实先生”,便是美学大师朱光潜。
朱光潜(1897—1986),笔名孟实,安徽桐城人,著名美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,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。著有《诗论》《谈美》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等,译有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》《歌德谈话录》等。
在谈及《诗论》时,朱光潜先生曾说:“在我过去的写作中,自认为用功较多,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,还是这本《诗论》。”

青年时代的朱光潜先生
《诗论》是朱光潜先生在美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,他用西方诗论解释中国古典诗歌,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,对诗歌的起源,诗歌在情趣、意象上的表现,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,诗与散文、音乐和画的关系,中国诗的音律,为什么中国诗走上了“律”的道路及现代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向作了深入的探索。
今天,我们向各位荐读朱光潜先生对诗歌美学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的论说。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提出的。朱先生在这一基础上展开论述,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,并援引西方文艺理论进行对比。跨越时空,这是一次大师之间的“美谈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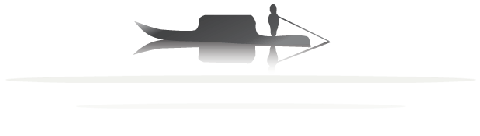

诗的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
文 / 朱光潜
(标题为编辑编加)
王氏在《人间词话》里,于隔与不隔之外,又提出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的分别:
有有我之境,有无我之境。“泪眼问花花不语,乱红飞过秋千去”,“可堪孤馆闭春寒,杜鹃声里斜阳幕”,有我之境也;“采菊东篱下, 悠然见南山”,“寒波澹澹起,白鸟悠悠下”,无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,以我观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;无我之境,以物观物,故不知何者为我,何者为物。……无我之境,人唯于静中得之;有我之境,于由动之静时得之,故一优美,一宏壮也。
这里所指出的分别实在是一个很精微的分别。不过从近代美学观点看,王氏所用名词似待商酌。他所谓“以我观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”,就是“移情作用”,“泪眼问花花不语”一例可证。移情作用是凝神注视,物我两忘的结果,叔本华所谓“消失自我”。所以王氏所谓“有我之境”其实是“无我之境”(即忘我之境)。他的“无我之境”的实例为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“寒波澹澹起,白鸟悠悠下”,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(所谓“于静中得之”), 没有经过移情作用,所以实是“有我之境”。与其说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,似不如说“超物之境”和“同物之境”,因为严格地说,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,都必须为 自我性格、情趣和经验的返照。“泪眼问花花不语”,“徘徊枝上月,空度可怜宵”,“数峰清苦,商略黄昏雨”,都是同物之境。“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”,“微雨从东来,好风与之俱”,“兴阑啼鸟散,坐久落花多”,都是超物之境。
王氏以为“有我之境”(其实是“无我之境”或“同物之境”),比“无我之境”(其实是“有我之境”或“超物之境”)品格较低,他说:“古人为词,写有我之境者为多,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,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。”他没有说明此优于彼的理由。英国文艺批评家罗斯金(Ruskin)主张相同。他诋毁起于移情作用的诗,说它是“情感的错觉”(pathetic fallacy),以为第一流诗人都必能以理智控制情感,只有第二流诗人才为情感所摇动,失去静观的理智,于是以在我的情感误置于外物,使外物呈现种错误的面目。他说:
我们有三种人:一种人见识真确,因为他不生情感,对于他樱草花只是十足的樱草花,因为他不爱它。第二种人见识错误,因为他生情感,对于他樱草花就不是樱草花而是一颗星,一个太阳,一个仙人的护身盾,或是一位被遗弃的少女。第三种人见识真确,虽然他也生情感,对于他樱草花永远是它本身那么一件东西,一枝小花,从它的简明的连茎带叶的事实认识出来,不管有多少联想和情绪纷纷围着它。这三种人的身份高低大概可以这样定下:第一种完全不是诗人,第二种是第二流诗人,第三种是第一流诗人。
这番话着重理智控制情感,也只有片面的真理。情感本身自有它的真实性,事物隔着情感的屏障去窥透,自另现一种面目。诗的存在就根据这个基本事实。如依罗斯金说诗的真理(poetic truth)必须同时是科学的真理。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。
依我们看,抽象地定衡量诗的标准总不免有武断的毛病。“同物之境”和“超物之境”各有胜境,不易以一概论优劣。比如陶潜诗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为“超物之境”,“平畴交远风,良苗亦怀新”则为“同物之境”。王维诗“渡头余落日,墟里上孤烟”为“超物之境”,“落日鸟边下,秋原人外闲”则为“同物之境”。它们各有妙处,实不易品定高下。
“超物之境”与“同物之境”亦各有深浅雅俗。同为“超物之境”,谢灵运的“林壑敛秋色,云霞收夕霏”,似不如陶潜的“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”,或是王绩的“树树皆秋色,山山尽落晖”。同是“同物之境”,杜甫的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,似不如陶潜的“平畴交远风,良苗亦怀新”, 或是姜夔的“数峰清苦,商略黄昏雨”。两种不同的境界都可以有天机,也都可以有人巧。
“同物之境”起于移情作用。移情作用为原始民族与婴儿的心理特色,神话、宗教都是它的产品。论理,古代诗应多“同物之境”,而事实适得其反。在欧洲从19世纪起,诗中才多移情实例。中国诗在魏晋以前,移情实例极不易寻,到魏晋以后,它才逐渐多起来,尤其是词和律诗中。我们可以说,“同物之境”不是古诗的特色。“同物之境”日多,诗便从浑厚日趋尖新。这似乎是证明“同物之境”品格较低,但是古今各有特长,不必古人都是对的,后人都是错的。“同物之境”在古代所以不多见者,主要原因在古人不很注意自然本身,自然只是作“比”“兴”用的,不是值得单独描绘的。“同物之境”是和歌咏自然的诗一齐起来的。诗到以自然本身为吟咏对象,到有“同物之境”,实是一种大解放,我们正不必因其“不古”而轻视它。

《诗论》
朱光潜 著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& 雅众文化 联合出版

20世纪中国学术经典
装帧考究、适合收藏
可以百读不厌的启迪之书


